|
20#
发布于:2010-01-30 15:50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Qasoqaanga与我们共同分享学习经历,回贴本身就是一篇朴实真挚的文章,读罢深受启迪。 终于又到周末了,总有想说说不完话,挤出空来继续叨叨几句…… 对藏缅语的兴趣是从很早就开始有的。当然,小时候还完全不懂谱系的划分,完全不知道藏语、缅语、彝语、克钦语等语言同属一个“语族”,而这个“藏缅语族”竟然不可思议地和一般人看来与之毫不相干的汉语同属一个“语系”。因为母语是阿尔泰语,我似乎天生便对S-O-V结构的粘着类型语言倍感亲切,在很长时间里,一直觉得藏语和蒙古语才像是“亲戚”,除了结构类型有相似处以外,二者间斩不断理还乱的文化联系也是令我产生这种感觉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真正作为谱系划分最关键依据的同源词,在没有任何语言学背景知识的人看来,远不及大量借词和结构类型相似那样显眼,汉语和越南语之间依然扑朔迷离的关系便是个典型的例子,与汉越间的相似程度比起来,藏蒙间的那点相似可谓小巫见大巫了。 提到我对藏缅语的兴趣,便不能不提纷繁奇妙的印度字母体系,缅文和藏文所使用的表记字母恰恰分属南北两大分支,分别显示了O形“圆润”和T形“骨感”和的极致。昨天读estrellas的文章,在对其热爱语言的执着深有同感之余,对部分内容略有不同见解,文字部分便是其一。个人认为,所谓“印度字母”,也即印度字母系统,和拉丁字母、西里尔字母和阿拉伯字母并不在同一层级上,后三者是现今世界三大通用字母系统,各自是用同一套字母拼写多种不同语言,虽然在不同语言中也会根据各自的语音特点增减少量字母,产生一些变体,但无论怎么变,主体部分总是相同的,是“书同字母”,这一点estrellas也提到了。举个例子说,无论法文的g,德文的g,还是越南文的g、马来文的g,写的话都是同一个写法,输入的话都是同一个字符。而印度字母系统中的g则在具体各种字母中各不相同(如下图,点击图片可查看清晰原尺寸),甚至倘若不认真研究的话已几乎完全看不出本是同源。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天城体字母,可说与上述三大字母系统类似,是用同一套字母拼写多种不同语言的书写体系。 图片:印度字母系统中的g.GI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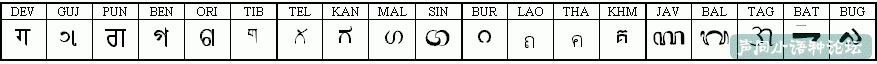
与印度字母系统处于类似地位的是包含了拉丁、西里尔等分支在内的希腊字母系统,包含了阿拉伯、希伯来等分支在内的阿拉马字母系统,以及阿姆哈拉文所属的撒巴字母系统。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所说的印度字母系统特指婆罗米字母系统,在estrellas介绍的印度字母两大系统中,佉卢字母可以确认的是阿拉马字母的分支,而婆罗米字母的起源则是一个长久争论不休的话题,但不论怎么说,婆罗米字母和阿拉马字母间的联系仅限于最初的拼音制度,而在字母形体和书写方式上,则完全可称得上开创了另一套与之截然不同的“音节”表记体系。以印地语为例,和其它印欧语一样,语音中存在着双辅音甚至三重辅音的现象,作为“音节”表记的印度字母记录这种发音时,采用了两个或三个同元音的音节,然后作相消的方法来表记这种发音,在字形上则看似合成了一个新“字母”。这种字母系统以“印度文化圈”为中心向外传播,向北影响到的藏文,向东影响到孟、缅文,向东南影响到作为孤立语的高棉、泰、老等族语言的字母书写系统,令它们类似地采用了“音节”表记的形式。所以说,无论藏文、缅文还是高棉文、泰文,都是印度字母体系中和天城文、孟加拉文、泰米尔文、泰卢固文等处于类似地位的文字,尽管各自都有“创制”的记载,但这种“创制”并非像韩文那样的独创(关于韩文的创制,虽也有汉源说和八思巴字源说等一些观点,但尚无足以令人信服的确凿证据,况且韩文除了在字形结构和横竖笔划上与之有所形似外,其音素文字的实质却与汉字和八思巴字迥异),而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继承和改造,在原先的基础上根据各自所表记语言的特点赋予了其新的属性。拿泰文来说,它的辅音和元音拼合时已不再是看起来合成一个“字母”,而是仍然保留了辅音字母和元音符号单独的原形,只是在纵横四个方向进行叠加而已,同时根据侗台语的语音特性增加了调号(另外顺带补充一点,关于estrellas所写的汉语和泰语比较一节,大部分内容确切来说应当是汉语拼音方案与泰文书写体系之间的比较,而不是两种语言的比较或两种文字的比较。汉语拼音方案只是标注汉语普通话读音的辅助工具,虽然按当初设计理念也确实是作为一种准书写体系来创制的,但到如今为止,它毕竟不是汉语实际的书写体系。像“一般汉语逢字必有声调,而泰语不是每个单词都用得到声调”这样的说法是容易起到误导作用的,说的意思其实是“在汉语拼音方案中,一般的每个音节都要标上调号,而泰文书写时并不是每个音节都要标注调号”。标不标调号,和用不用得着声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汉字从来就没有调号,但却不等于没有声调)。老挝语和泰语是两种亲缘关系极其近的侗台语,所使用的文字也同出一脉,发展到现今,或许我们已经看不太出它们的各个字母和高棉文各个字母间具体的对应关系,只是觉得整体看起来形态有点像而已,然而泰、老这两种亲缘关系极其近的字母间对应关系依然是比较显而易见的。在书写形态上,老挝文比泰文笔划圆一些,有观点认为是受了缅文一些影响。而泰文和高棉文发展至今的通用字体则偏近长方。 回到藏缅语的话题上来,藏文的正字法,既不像天城文那样“合成一个字”,也不像泰文那样仅仅是在辅音的前后左右加元音,而是另一种“加字”的“十字架”形结构,除了元音符号加在上下以外,辅音字母也作为“加字”加在“基字”的四个方向,其中加在前后的看起来仍然是截然分开的不同字母,而加在上下的则紧密连结并在字形上发生变化,看上去有点像是稍微长高了的一个“字母”,这种结构形式和藏缅语的单音字特点决定了音节与音节之间不能像其它印度字母系统文字那样连成一体,而需要用一个断点来将其分离开来,否则就会出现前后争字造成音节混乱的情况。 藏缅语中绝大多数语言和方言也是有声调的,但无论藏文还是缅文,都不像泰文那样采用单标调号的形式,而是在辅音字母的元音符号组合的形式里已“蕴含”了声调信息于其中了。通常认为,原始藏缅语是没有声调的。后来由于语音和音节的简化,才开始使用声音的高低来区别不同的音节,作为加强辨义的手段。藏语卫藏方言的声调比汉语产生得晚很多,而保留了大量复辅音的安多各地方言至今仍然没有声调,康方言区则介于二者之间,语音结构也呈渐变的带状分布形态,其中分布在昌多地区北部巴青、丁青一带、那曲地区和玉树州的牧区次方言近于安多方言,但却有了声调,导致这种情况的除了文化接触方面的外因,声母清浊和韵尾舒促则是声调发生和发展最关键的因素。藏缅语言声调起源研究中,无论清浊说、长短说、松紧说、韵尾说还是声母说,都不外乎以音节形式的简化或变化为前提。声调发展与声母清浊、韵尾舒促之间的关系,在藏缅语中是一种较普遍现象。 相比藏语而言,缅语作为藏缅和侗台、孟-高棉、印欧语言交会地带的一个语种,在语音上呈现出一些有别于藏、彝等语言的不同特点,譬如长音、短音的区分,无论长a还是短a,在发音时均有一个轻微的擦音h,这在藏缅语中是不多见的。缅文字母按传统的分法,根据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的聚合分为八类,其中第三行和第四列字母多是用于拼写巴利文借词,在现代缅文中已基本不用。由于缅语不分鼻音和齿音,为了便于和第二行区别,通常将第三行5个辅音按齿音来读。缅语既有声调也有复辅音,辅音中没有颤音,r和y常可通用。 适当地运用一些语言学基础理论对所学目标语言进行把握无疑对学习会起到一定帮助作用,但并不是说,想要学好语言就一定要在钻研语言学知识方面下极大功夫,我认识的朋友中,有许多人虽然只有很浅的语言功底,但却仍能将一种或几种语言学得很扎实很地道。关于学习途径和方法,不同人各有各的见解,适合于一个人的套路未必适合于其他人。不论学任何小语种,大多人在起初都会说,没有基础,没有环境,没有教材,没法上培训班,学校没开选修课,也没多点银子,没多点时间……怎么办?我和大家一样,什么都没有,但这并不是没法学的理由。网络是个神奇的东西,这种神奇,最重要的还不仅仅是在于只花很少银子的代价就可以获取大量多媒体学习资料,而更是在于让我们有了和懂这种语言的人甚至使用这种语言的人进行直接交流的可能,这也就为我们不断进步提供了不竭的源泉。鲜活的交流,才是真正无限的资源。因为自己本来在语言方面的素养就很差劲,再加上工作极为繁忙,生活的担子还很沉重,无法抽出太多时间投入到学习中,我从来不曾有过一生要学会多少多少种语言乃至学好多少多少种语言的远大抱负,但一旦下定决心学习某种语言时却必是要脚踏实地去努力的。这方面做得很好的声友不乏其人,像小自在天、sindy迪迪……他们不是现在所学语言专业的科班出身,从事的不是和现在所学语言有极大关联的工作,甚至语言学习并不是他们唯一的业余兴趣,像其它比如文史方面他们也各有所好。可以说,他们是语言爱好者中近于“凡人”的一类,他们的学习模式不但很成功,更重要的是,我们大多朋友都可以借鉴可以参考。他们学习进步的点滴没有“神助”,他们在所走的道路上没有跨出只有“绝世高手”才能跨出的“飞跃”,而是每个脚印都清晰可辨,让人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大多人眼中所谓的“神奇”,只要把寻找那“神奇”的时间花在实打实的学习上,其实原本就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梦想。 ……又有事得出去了……暂写到这里吧……希望和大家相互交流,共同进步! |
|
|
|
21#
发布于:2010-01-30 14:15
再看了一遍,感觉很亲切呢,呵呵~
|
|
|
|
22#
发布于:2010-01-25 13:32
楼主这是我所向往的. 真的.真的.真的...
|
|
|
|
23#
发布于:2010-01-24 21:17
本帖最后由 Qasoqaanga 于 2010-1-25 08:25 编辑
很真實的感言,移動了Qasoqaanga。 我始終不認為我的母語是普通話,上海話(包括浦東話、寧波話和蘇州話)則是真正的母語。普通話僅僅是無可奈何的交際工具。然而現代規範的漢文和古代書面語則是Qasoqaanga始終如一的書寫語言,儘管用德文寫過一篇粗糙的遊記,用拉丁文寫過索要書籍的信函和用蹩腳的英文充當對外的聊天工具。高考應試的俄文成績是砰砰響的,但時過境遷已經剩下能勉強朗讀一遍的能力了,這還得歸功於俄文拼寫比較規則的緣故。 由於以前工作的緣故,外語是不需要的,因此從沒有用心學好一門外語,僅僅是靠五分鐘熱度去學一門外語和民族語言。前後學過大約十門外語和五門民族語言,可見更換之頻繁。這主要是沒有需要只有興趣。不過Qasoqaanga很是為自己的自學能力驕傲,似乎沒有什麽語言能阻擋Qasoqaanga在最短的時間內入門,能很快朗讀、寫最簡單的句子和查閱單語辭典。前陣子友人幫忙打印了一本純拉丁文的詞典,如獲至寶。正因為入門快也廢棄快。Qasoqaanga很不喜歡非羅馬字希臘字基利尓字以及梵字之外的語言,主要是容易忘記。 Qasoqaanga十分癡迷文史哲,尤其是我國古代和希臘羅馬的文學與哲學。這方面看的書委實不少。因此,喜歡拉丁文和古希臘文是理所當然,相關的工具書也最伙。喜歡二戰的的朋友很多,Qasoqaanga不例外,德文的自學自然就趕在了英文之前,其目的僅僅是爲了看懂德軍的軍銜和隆美爾的作戰計畫原文。記得以前有幸和一位德國在Nankingstrasse散步,并主動介紹建築物,介紹租界歷史,用的是英德混合語。那位朋友可能是出於友善,也使用英德混合語交流,此為笑談。俄文是第一門系統學習的外語,很可惜報廢了,已經沒有使用價值了。在碰到書刊中有人想用俄文字母糊弄,Qasoqaanga還能辨別,僅此而已。 自學梵文,以前一直有打算,一是沒有時間,二是沒有資料。真正的開始是在看了季羨林大師走了的新聞之後,本人才開始大肆搜羅梵文資料,從聖彼得堡梵文大辭典到各類英德文版的教科書,再到梵文作品的搜集,可以說再搜羅下去已經沒有意義了。從2009年十月一日在家休息開始看字母表,大概三四天對梵文的拼寫、連音規則等正字法內容徹底弄明白了。目前反復記憶動詞屈折變化,打印成文地鐵里反復看。對於梵文,Qasoqaanga並不是要去翻譯什麽,而是要比較梵漢對音和佛經翻譯。玄奘是Qasoqaanga第一位的語言大師偶像,梵漢通達程度季羨林大師亦弗及也。玄奘的譯文是學院派風格,是將漢文發揚光大的一個里程碑。對於一位對本土文化的癡迷者,看不懂漢文最輝煌的兩種高峰——六朝駢文和奘譯佛經,是一位受過高等漢文教育的漢人的一生的恥辱。本人不信教,奉行茍有用無不用之原則。 Qasoqaanga以前的專業決定了對語言學的癡迷,本人的籍貫決定了對吳語的偏執。古漢語及其相關的音韻學、方言學一直是Qasoqaanga最熱衷的學科。中古音韻是方言研究的基礎,上古音韻是研究漢語和親屬語言關繫的紐帶,也是讀懂先秦文獻的必要知識。拉丁文的疑問詞大都是Q開頭,因此語言學家稱之為拉丁文Q詞,也許印歐語是Kw詞。反觀古漢語也有類似的M詞,那就是否定詞絕大多數是M開頭,譬如無亡莫。諸位也許不知,普通話的韻母u在上古大部份念a,嗚呼其實念成aha,我nga(比較藏緬語),父ba,擬音很粗糙,說明問題就行了。學習中古音的傳統方法是學習《廣韻》這部漢語語音根目錄的書籍,但是最鮮活的語音資料那只能是隋唐的梵漢對音。菩-提-薩-埵,梵文對音為bo-dhi-sat-tva。從對音中,《廣韻》代表的中古漢語語音系統得到了驗證。同時梵文的翻譯,直接導致了古代拼音方案——反切——的產生。從此中國人有了韻母和聲母的完整概念。西域胡僧的蹩腳漢語水平,使得漢語口語因遷就梵文文法的漢譯佛經的誦讀而發生了有記載的裂變。現代漢語和古代書面語的高度脫節,除了語言發展的歷史因素之外,梵文至於中古漢文、倭文至於現代漢文之因素起了推動作用。 目前Qasoqaanga在閒暇之餘,用功的只有拉丁文和梵文。這是東西文化的底層語言。現代西文和倭棒文沒有很大興趣去入門,沒有實用價值和學習動力。能看看英文的行情分析、查查德文版的聖彼得堡大辭典足够了。吳語的興趣將陪伴一生,格陵蘭語要看看是否有同好者。一切就這樣下去了,就看諸位壇友有什麽動人的帖子了。 |
|
|
24#
发布于:2010-01-24 21:03
如果说学习真有什么秘诀的话,那无疑就是,交流,交流,再交流
我同意 |
|
|
上一页
下一页





